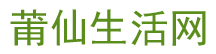几个月前,家对面的街上开了家布鞋店。一直以来我对布鞋有着特殊的情感,那天下午,我不知不觉地走进了这家店。
小时候的我像个男孩子,短发、矮小、黑瘦。早上一睁眼,胡乱抹几下脸,扒拉几口饭,套上一双布鞋便跑出门玩去。家里那只阿黄也摇头摆尾,蹿出老远,撒着欢儿在我左右跑来跑去。
父亲身体不好,只能干些轻松的农活,家庭的重担几乎都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母亲大部分时间都在田里劳作,一旦得空,便搬一把小板凳,和隔壁几位婶婶坐在院门前的空地上,或织毛衣,或纳鞋底。
长期干农活的缘故,母亲的双手布满了老茧,因皲裂缠满了胶布,但她做千层底的双手仍是那么灵巧。鞋底是用一些碎布头做的,那时候不舍得用面粉熬糨糊,都是用剩饭面汤将一层又一层的布头粘在一起,放在太阳底下晒干。一家四口的布鞋都是母亲一人缝制的,四个人的鞋样母亲都小心地压在箱子底下。在晒干的袼褙上照着鞋样剪下八九个单片,用白布包边,再将单片摞在一起,拿麻线缝制。这麻线是自己搓出来的细麻绳,牢靠,不易烂。母亲的中指上戴着顶针,那时我总喜欢叫它戒指,针扎进鞋底前母亲总要在头皮上蹭几下,我曾特别担心母亲会刺伤自己或将头皮磨坏,后来才知道这样可以润滑针。母亲用顶针顶住针尾,用力地穿过鞋底,在另一边也用力一拉,便拉出一条细细长长的麻绳。
母亲喜欢将鞋底缝成一圈一圈的,由外到内,又细又密,缝完后给人整齐的美感。别看母亲纳鞋底时说说笑笑的,实则是个耗精力的活儿。一只鞋底母亲断断续续要缝好几天,那几天母亲的手上总有拽麻线勒出的红色沟痕,被针扎到手更是家常便饭。
晚上我在一边写作业,母亲就坐在另一边纳鞋底,两人共用一盏昏黄的灯。四周静悄悄的,而我的心里全是剪刀与桌面的碰撞声,顶针与针之间清脆的金属声,线穿过鞋底时的Www.0279.NeT摩擦声,这些美妙的声音伴随了我的整个童年。我与母亲这样静静相处的时光不多,这种时光成为我心中珍视的回忆。
这种场景我已多年未见,这种声音我已多年未听,关于千层底的记忆却一直根植在心中。这种记忆不同寻常,它像是一本老相册,温暖,经得起坎坷,经得起变迁,经得起平淡,经得起离别,经得起岁月的沉淀。
我穿着母亲纳的千层底走到镇上,走到县里,走到城市,走进高中,我的行囊里还放有几双母亲做的鞋。一人在他乡,这些布鞋成了我唯一的情感寄托,我仿佛能看见家人对我的期盼。我将对故乡的思念存放其中,一步步走向远方。
我明白自己与这座城市的格格不入,尽管如此,我仍坚守着自己对千层底独一无二的钟爱。我穿过时尚的运动鞋,精致的皮鞋,但我一直备有一双千层底。它带给我的不仅是舒适,更是一种安全感。
那家布鞋店开张前没有宣传,开张时没有横幅、鞭炮,它只是静静地开了。一排排鞋架上放着一双双整齐的布鞋,它们不似以前那样单一,只用一种纯色的布做成,而是有了更多的色彩,有了现在流行的元素,但又不失最初的模样,简单中带着典雅,朴素中带着丰富的情感。这些布鞋不需要明亮的灯光,不需要饰品的镶嵌,它天生散发出一种属于自己的魅力,像一块磁铁,不知不觉地吸引你的注意。
那天我在那家店买了一双布鞋,我将它放在了母亲为我做的布鞋的一旁。这些年母亲仍在缝制布鞋,只因我常常念叨,常常于不经意间流露出自己对它的情感,母亲便一直没有放下手中的针线,想做我一辈子都穿不完的布鞋。
每每看到这些布鞋,我就像回到夏季那些美丽的清晨:一群女生在大门口踢毽子,小溪在山间和路边流过,妇人们蹲在溪边拿棒槌敲打衣服,院门口撑起的竹竿上晾着花花绿绿的被套。向山的一边望去,一轮初升的太阳,正衬着一片清澄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