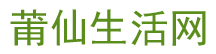摘 要 特别权力关系领域不能完全排除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对特别权力关系领域中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事项宜由法律直接规定,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对于基本权利之外的其他管理事项,宜贯彻自治原则,可排除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和司法救济,以保证特别权力主体管理功能的发挥。
关键词 特别权力关系 法律保留原则 自治
作者简介:李坤,复旦大学法学院2023级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法学。
特别权力关系领域是否应当引入法律保留原则,关系着该领域中公民权利能否得到司法救济,关系着社会生活中自治与法治的关系,其重要性不言自明。我国现实生活中也存在着特别权力关系领域,这些领域基本排除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对法律保留原则的完全排除往往引发一些社会问题,如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学生状告高校案件、社团成员状告社团组织的案件等等,这些案件往往被排除在行政诉讼范围之外,不利于公民权利的保障。但反过来说,如果在这些领域完全适用法律保留原则,则不利于特别权力领域内自由管理作用的发挥,与当代的社团自治趋势相悖。
一、特别权力关系理论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最早是在19世纪后半叶由德国著名公法学家波尔?拉贝德创立的。他认为“国家方拥有权力与相对方自由加入是构成特别权力关系的基本要素和特征” ,这构成了最原始的特别权力关系基础理论。德国行政法学家奥托?迈耶在波尔?拉贝德理论的基础上对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展开更深入的研究,树立了完整成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体系。奥托?迈耶认为“人民与国家之间基于法律事实(如基于法律规定、行政处分或利用公共设施)会构成一种特别的权力关系”,“其主要类型有公法上的勤务关系、公法上的营造物利用关系以及公法上的特别监督关系等”,他特别强调“在特别权力关系中,依法行政、法律保留等原则不再适用,国家可以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限制行政相对人的自由,而相对人不得对此提起争诉”。
二战结束后,随着人权理念的兴起与发展,“司法国”理论在德国兴起,该理论主张法院拥有对行政行为的完全审查权从而来保障人权,之后的一系列立法也否定了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对法律保留原则的完全排除。这个时期,德国公法学家乌勒提出将特别权力关系区分为基础关系和管理关系,对于基于基础关系所作的行政处分,相对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对管理关系则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该理论修正了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但由于基础关系和管理关系界分的模糊性,这一方法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况且“管理关系”中的一些行为往往也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把这些行为排除在司法审查范围之外也不利于公民权利的保护。“基础关系和管理关系区分说”之后被“重要事项保留说”取代。
我国公法上虽然没有对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进行明确的界定,但是实践中确实存在着特别权力关系。特别权力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不可替代性,即便是法治发展到更高阶段亦如此。特别权力关系领域中的基本管理规则一般都是由行政机关、社会团体或者高校等特别权力机构自行设定,排除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这样一来,就不利于特别权力关系领域内的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同样的,如果在这些特别的领域内完全适用法律保留原则,则对特别权力关系所维系的体系功能产生不利影响。对法律保留原则是否应当适用于特别权力关系领域,根本上是取决于对两种利益价值的取舍,维持特别权力的运行以达到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功能从而保障多数公民的公共利益,还是保障特别力相对人在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以及与其他普通公民宪法权利的平等性,孰轻孰重。在对这两种价值进行衡量的基础上,再对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与否进行探讨。
二、法律保留原则
法律保留原则起源于君主立宪时期,最早是由德国行政法学家奥托?迈耶作出了明确的定义。他认为行政权只有在获得法律授权的前提下,才能对人民的财产与自由进行干涉。史上法律保留原则主要有侵害保留说、全部保留说、重要事项保留说等。其中重要性理论是指涉及到相对人重要的基本的权利义务的行政行为应当由法律规定。重要性理论根据调整事项的重要性程度,将法律保留分为绝对法律保留、相对法律保留和无法律保留三个层次。
我国的法律保留制度更接近于重要性理论。我国现行《立法法》第8条和第9条全面引进了法律保留原则,对法律保留事项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这两条所规定的法律保留原则实际上可以分为法律的绝对保留和法律的相对保留。随着时代发展,“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范围开始扩大,不仅仅停留在侵害行政领域,而要扩大到内部行政、给付行政等行政领域” 。尽管《立法法》对法律保留原则的规定已经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但我国目前的法律保留原则还是存在许多问题的,尤其是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范围方面,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保留范围及其狭窄。在那些特别权利力关系领域,公民的基本权利保护是排除法律保留的。笔者认为,随着法律保留原则适用范围的的进一步发展,将其引入到特别权力关系领域中来未尝不可,只是这种引入必须考虑到我国的现实情况,不能一厢情愿地只顾追求绝对的法治主义,而忽视特别权力关系所维系的那些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系统。
三、自治与法治关系视角下的分析
特别权力关系领域是否应当引入法律保留原则,还要考虑当前社会自治与法治关系的发展走向。当前正处于传统的管理行政向现代的服务行政转变的时代,一味地强调行政主体的社会管理作用有点不合时宜。随着社会民主实践的发展,传统的议会民主理论逐渐被新兴的参与民主理论取代。新的参与民主理论认为,人民主权不能全部委任人民代表机关行使,社会管理公权力也不能全部委任政府来行使,人民只是将一部分权利转让给代表机关及政府,其自身还保留着大部分权利。一方面公民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来参加国家管理,另一方面就是公民可以通过参与各种自治组织行使部分社会管理公权力。在政治国家存在的条件下,社会自治组织的自治是相对的,其仍要受到国家的管理和监督。自治组织只能在自治范围内行为和活动,除法律法规授权外不能对外部相对人实行管理行为和采取行政制裁性或强制性措施。自治组织内部章程不能对内部成员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进行剥夺和限制,对这些事项的规定只能有法律来作出。 高校、社会团体、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自我管理都属于社会自治的范畴,这些组织、团体与其成员之间除了一些可以通过民事法律来调整的关系外,还存在着某些特别的管理权,这些管理权实质上带有行政管理权的性质,如高校开除学生、社会团体对其成员的资格的取消等等。对于相对人的这些权利的保障,无疑更适合通过行政法律来调整,但由于在社会团体自治观念的影响下,对这些特别的管理权与普通的民事管理权没有进行区分,在救济途径方面没有进行特别的规定,因此这些特别权力相对人的某些特定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平等的保障。虽然发挥特别权力机构的自我管理功能无疑对这些领域内部的功能发挥有明显的保证和促进作用,但内部的自我管理如果得不到外部的监督则有可能造成特别权力的滥用,从而损害特别权利相对人的基本权利,这样也是明显的不公正。最好的做法是能够做到两者兼顾,既要保障特别权力功能的发挥,也要保障特别权力相对人的权利,因此在特别权力关系领域内引进法律保留原则,对重要性事项进行保留,由法律来进行规定,是一个较为合适的选择。
四、 特别权力关系领域内的“重要性事项”适用法律保留
在特别权力关系领域内,对那些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性事项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对于其他的管理事项则可以由法律授权特别权力机构或者直接由特别权力机构自我管理。对于法律保留的事项,当特别权力相对人的权利遭受损害时,可以付诸行政或司法救济。除去法律保留事项外,其他的特别权力关系领域内仍然排除行政或司法救济,由特别权力机构自行处理,坚持社会自治主义。笔者认为结合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在特别权力关系这一特别领域内,所有事项都适用法律保留原则不利于特别权力机构管理职能的发挥,与当今社会自治的趋势相背离。可以采取折中的做法,通过立法对重要性事项作法律保留,一方面可以保障特别权利相对人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又可保证特别权力主体的自主管理权,这样一来有利于缓解当前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两种价值的冲突。当然,对于特别权力关系中重要性事项和非重要性事项的界分也是很模糊的,缺乏可操作性。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完善立法的方式来进行,通过法律明确规定什么是重要性事项。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治的进步,再通过修正法律来调整重要性事项的范围。
对于法律保留原则是否应当适用于特别权力关系领域内的争议,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两种结论都有自己的利弊。结合特别权力关系在我国当前现实条件下所发挥的巨大的管理功能以及当代社会自治趋势的取向,与其完全地摒弃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而实行不切实际的绝对的法治主义,损害社会的其他民主制度及其稳定秩序,不如从立法上承认特别权力关系,赋予其合法性,进而再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和修正,从而实现管理功能所达到的社会整体效益与个人基本权利的平衡。对直接关系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性事项进行立法界分,也不必然地造成立法机关的压力,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而对重要性事项以外的其他管理事项,由特别权力机构内部规则进行调整,发挥特别权力机构的自主性、积极性,也符合当代社会自治主义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