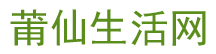初次品读到“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时候,还只是匆匆的一瞥。我仅仅感觉到那无尽的愁思和哀婉,却走不到词人的心里。于是,我开始翻读历史的书卷,想要在浩瀚的时光中,拾起尘封的记忆。
李煜,生于南唐升元元年(937年)七夕,因其一目重瞳,貌有奇异,遭长兄太子猜忌,为表明其志在山水,无意争位。李煜苦心钻研诗词歌赋,自号“钟隐”以期避祸。
然,事与愿为,本为第六子的他,被迫推上皇位,唱了一出造化弄人,难以言表。本无政治才能的李煜被推上了不该属于自己的高位,短短十几年时间,就落了个家破人亡的下场。就此,千古词帝落幕,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
楼上人不在,楼下人又来,匆匆一过眼前人,漫漫飘零身后名。该是怎样的月色才能描绘出孤寂的痛恨,那广漠无边的天地,黑漆漆的,空洞洞的。会不会是城楼的阁太高,将月色洒的太满,留下了月夜的无边无际。又或许是天上的星太暗,照不亮来时的路,让愁苦锁在了阁楼中,走不了,逃不掉。李煜独上西楼太苦,“锁清秋”干什么?也好过一个人。
我总是在想,若他没有被推上皇位,又该是一副怎样的光景,是否活得更精彩一些,最少,也能寄情于山水吧。是非对错转头空,原来不由自主是真正的无奈。都言生到帝王家是多么幸运的事情,可李煜或许更喜爱山水田园的快乐,在这淡淡的花季里过完自己的一生。不是不愿,而是不能,且看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也落了个垂泪对宫娥的下场。想来,再深深的富贵,对于李煜来说都是枷锁和牢笼,困于其中的诗词,落满灰尘的工具,总也不能再次把玩,沉重的夜里,回忆起自己的一生,该是如何的悔恨和不甘。
“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在梦里回转片刻的温暖,那虚假的欢愉或许是些补偿。他尚且知道那是梦,“贪欢”,多少带着些奢望。从君临天下到阶下之囚,短短的光景,活得不再是自己。“违命侯”多么可笑的名字,简直写尽了他悲惨的一生,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残存和破碎,根本无法留下自己,在记忆的深处中,有且只有一段为人皇,为人者的记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其结果,注定是悲惨的,亲手为自己画上一段悲剧的人生,其痛苦,必定响彻身骨。李煜,用尽力气也走不出这宫墙的牢笼,读不懂自己,也读不懂别人。即使化作这燕雀的双翅,也很难飞出这宝座的高度。承受着生命难以匹敌的力量,又用尽力气去搬运,去回转,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人去楼空,悔恨不已。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来去也匆匆。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他用自己的一生去为词做贡献,用经历成全自己的词作,为了“千古词帝”,他付出了所有,乃至生命。他是有梦的,梦里何尝不可以君临天下,即使皇冠上挂满了耻辱,也有自己的词作陪。那回转百千回的梦里,流淌的又何尝不是自己的寄托。他是懦弱的吗?或许吧,他本身就懦弱的活着,懦弱的走着,懦弱的当上了皇帝。可是,他又坚韧着,不屈着,不甘着。一首首绝美的词唱了出来,又何尝不是他活着的证明?
兜兜转转,像极了一个轮回,他,李煜,在他生日那天,写了一首词《虞美人》。他或许知道些什么吧,狂妄的笑着,张扬着。没有什么事情能阻止这个人的倔强,也是他作为一个词人最后的反抗。这一曲罢了,留下了千古的绝唱,又何尝不是一种成全。一杯毒酒而已,活着不如痛快的死去,至少在这生命的最后,也肆意潇洒了一回。
是啊,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缓缓的流着,也不轰轰烈烈,也不悲壮。燕子飞着,回转着,山水匆匆,流转着不过是一个过客。疯狂生长的田野里,肆意妄为。日日夜夜的想念,都将化作这一词一阙中,至少缓解了心里的委屈,减轻了厚重的耻辱。
李煜,或者,李后主。用词写出了自己的一生,甘与不甘只在一瞬间,敢与不敢也只在一瞬间。没有人会说李煜的不是,都在夸赞他词作冠绝天下,他成功吗?他是成功的,若不是这词,何以在这慢慢无边的历史中,留下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其实爱极了李后主的词,每次品读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若是有空闲,总愿搬一把小椅,寻一个有雨的日子,捧一卷词,读上一整日。李后主的词是极有魅力的,每每读着,总也不愿放下,感受其中的孤寂,也能琢磨好久。
我想,李煜终究也是放下了所有,释然之后,也就没有那么不甘了,他这一生啊,就像冷傲的寒梅,即使曾经傲立在枝头之上,与万物争香,也抵不过零落成泥,落花飘零。何时再听他唱一曲。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作者:程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