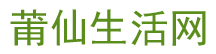文丨笔杆先生
编辑丨笔杆先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取向:国际承认、维护完整、在国际关系中的定位在外交层面上,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关系非常好。鲜为人知的事实是,苏联代表团在联合国筹备委员会的会议上坚定地捍卫了“捍卫斯塔诺杰·西米奇第一次被苏联代表团提名为秘书长候选人”的提议,与此同时,它也不失时机地揭露了其“捍卫南斯拉夫当选安全理事会成员提议的动机”。
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萨奇科夫(I. V. Sadchikov)的外交报告充满了对南斯拉夫社会状况的赞扬,有助于建立和谐的关系。其中一张1945年12月的照片提供了说明。
大使在与农业部长瓦索(Vaso ?ubrilovi?)的访谈中指出,他被告知“直到最近,在南斯拉夫领土上,苏联和西方盟国的外交政策界线还被越过……”但是,现在可以说,由于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胜利,斗争已经结束了,他们还说,这些战线现在已经转移到匈牙利、法国和罗马尼亚。党际关系表明,没有理由担心。
从1946年开始的所有报告都表明,共产党是南斯拉夫政治进程中的一个关键角色,是南斯拉夫唯一真正的政治力量……它已经拥有24万名会员……南斯拉夫的“党”一词与苏联的意思相同。
在意识形态方面,没有偏离十月革命的道路,因为每一次都表明,“同志们指出南斯拉夫共产党是按照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组织原则组织起来的”。
我们可以感觉到1947年初的不和谐的音调。这方面的一个指示性例子是苏联大使a . J. Lavrent题为“南斯拉夫简要回顾”的外交报告。该报告在某些部分证实了南斯拉夫对苏联的承诺,指出“苏联的政治支持是加强南斯拉夫国际地位的主要因素”。
“225名学生和25名毕业生”的数据证明了两国人民层面的合作,目前的外交政策完全依赖,称“南斯拉夫政府的外交政策完全面向苏联”。
南斯拉夫社会的谴责不应被忽视。官方形式的国家通信的第一个例子是对南斯拉夫领导层行为的评论。它们在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过分强调当地情况的特殊性”)、历史的(“突出南斯拉夫游击队运动的重要性,而削弱苏联在解放中的重要性”),以及政治的(“与苏联有关的寄生情绪”)。
整个1947年都致力于执行已经达成的协议。他们成立公司,就经济和技术援助的动态进行谈判,并考虑到在国际舞台上的一致表现。
苏联作为南斯拉夫外交政策支持者的态度继续存在。我们可以在几乎每一份通过外交渠道的官方通信中看到这一说法的证实,这些外交渠道要么是通过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要么是通过波波维奇大使在莫斯科的官方通信。
当英国和法国大使在一次联合访问中呼吁西米奇部长参加欧洲国家会议,讨论美国的经济援助计划时,拉夫伦季耶夫大使说,西米奇部长告诉他,“南斯拉夫政府可以立即给出否定的答复,但仍有必要征求莫斯科的意见”。
在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良好的最后一年(1947年),在国际舞台上的一致表现在联合国最为明显。当时从贝尔格莱德发往莫斯科的外交电报几乎每天都提到它。
铁托说,南斯拉夫政府同意苏联提出的选举乌克兰而不是波兰为安理会成员的建议。但是,如果这个候选资格不被接受,铁托认为应该提名南斯拉夫,而不是捷克斯洛伐克。
首先,南斯拉夫希望当选是因为安全理事会正在审议希腊问题;正如铁托在解释联合行动请求时所写的那样,捷克斯洛伐克的候选资格不会加强共产党的国际声望。
1947年社会主义世界中最重要的进程是一个伞形组织的形成,该组织将所有共产党聚集在一起,目的是在国际关系中协调和共同出现。正如日丹诺夫在1947年9月26日对各共产党代表进行咨询时所强调的那样:
确保公正的民主和平的任务把反帝国主义和反法西斯政治阵营的所有力量联合起来了。在此基础上,苏联同民主国家在所有外交政策问题上的友好合作得到了发展和加强。
在大国相互对立的倡议(如杜鲁门主义或马歇尔计划)的背景下,日丹诺夫还指出,有必要“协商和自愿协调某些方面的行动”,所有这些行动的最终目标都是“为民主和平而战,为消灭法西斯主义的残余和防止法西斯侵略的重新出现”。确认各国人民平等和尊重其主权的原则,在总体上全面削减武器。
根据决议第5项,贝尔格莱德被指定为新闻局总部。因此,南斯拉夫将自己置于这个组织的最顶端,尽管它宣布其所有成员一律平等。Informbiro成立的那年也是十月革命30周年。铁托在祝贺斯大林时,保证继续实行一贯的政策,他说:
在十月革命三十周年之际,我们向你们保证,我们将维护南斯拉夫人民同苏联人民之间的真正友谊,坚决捍卫伟大的十月革命的遗产,它保证全世界民主与和平的胜利。
在1940年以前,南斯拉夫和苏联之间没有任何国家间的关系,苏联共产党同南斯拉夫共产党(有6000多名党员)的关系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法律和惯例进行的。
除了在双边和多边关系中站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倡导者的前沿之外,南斯拉夫的领导层并不是从外部“引进”的,而是从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中脱颖而出的,这为后来对南斯拉夫的不结盟政策奠定了基础,并成功地管理了30多年。
结论正如我们已经确定的那样,CPY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几乎所有时期都在使用非法的通讯渠道。另一种有条件地从苏联布尔什维克那里继承下来的组织形式。
十月革命的研究人员试图找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策制定的最初阶段,在许多情况下,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主要是因为缺乏这一时期的文献。
就像在南斯拉夫一样,关于苏联社会主义长期时期的记录在今天是不完整的,因为“他们政党的地下存在和阴谋性质,以及内战期间大量文件的破坏,确保了10月的书面资料很少”。
其他信息来源很难被认为是可靠的科学信息,因此,任何“热衷于使用个人回忆来提供最近的过去的连续性、连贯性和色彩,都被对记忆变幻莫测的普遍不信任所削弱”。
在南斯拉夫观察到的十月革命的另一个遗产是“作为政治修辞基础的同样的革命话语蒙蔽了学术分析的方式”,这种由于意识形态热情而偏离对历史事件的批评“不利于学者们对自己的概念、欲望或偏见进行重新审视”。
另一方面,对南斯拉夫在1945-1947年期间的外交政策实践的分析表明,南斯拉夫对战后世界的组织采取了积极的态度。
在全球层面上,“南斯拉夫满怀信心地求助于联合国,从大会第一届会议开始积极参与联合国的工作”,在尊重外交政策始于国家边界这一古老格言的同时,它通过承认“南斯拉夫的民主政府”表现出非常建设性的态度
并与保加利亚建立外交关系,而不是等待签署和平条约,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在巴尔干地区实现密切合作。虽然这不是作者的中心关注的主题,但我们注意到1946年南斯拉夫的主要外交政策问题是从7月29日持续到10月15日的巴黎和会。
它要求通过同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提出的和平协定草案。除芬兰外,所有国家都是南斯拉夫的邻国,议程上的解决方案与这个新国家的形成阶段直接相关。这一时期的问题也出现在与希腊的关系上。
也就是说,在国内内战的过程中,通过将辩论转移到联合国安理会,同时指责邻国(包括南斯拉夫)在武装冲突期间帮助各方,冲突出现了一种国际化。
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应对所有它所面临的问题是明确的:我们正在与苏联,因为我们听到不断从苏联和平的声音,而我们经常听到关于原子弹和战争威胁西方的,提托说的公开FNRY总理和国防部长在FNRY国民大会3月31日1947.83为什么与美国的关系不是更好?
在我们看来,在同样的exposé中,铁托非常形象地解释了这一点,分析了当时美国驻南斯拉夫大使的行为。正如他在国民大会上的讲话所说,美国“不断地干涉我国内政,助长我国国内的反动,换句话说,这意味着阻碍我国的巩固,另一方面,美国公众对新南斯拉夫的持续诽谤报道”,特别强调官方外交报道很可能是“不正规的”。
这无助于建立良好的政治关系。要分析的南斯拉夫外交政策的最后一个时期(1947年)的特点是出现了三个关键问题:
(a) 上文提到的解决希腊政府指控其干涉国内武装冲突问题的办法;
(b) 创建Informbiro;
(c) 与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签署了《友好合作条约》。
这些也是南斯拉夫外交政策的决定因素,导致了1948年之后的根本性转变。
关于为什么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关系在1948年破裂的争论很有趣。佩特科维奇教授从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苏联的三位一体关系和1947年事件的年表中看到了这一点,即从1948年初开始。铁托和季米特洛夫于8月1日签署了《布莱德协定》,同年11月27日又签署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然后,《真理报》(Pravda)(1948年1月20日)发表了文章,不同意季米特洛夫的观点,对建立巴尔干联邦的想法充满了负面情绪。佩特科维奇教授在1948年2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三方会议上看到了危机的顶峰,该报告是在最高级别上提出的。
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也在场,铁托任命卡德尔吉、吉拉斯和巴卡里奇为他的特使南斯拉夫两年的外交政策由此结束,这一政策的范围从苏联政策中最突出的对十月革命思想的支持,到以不结盟外交政策为体现的南斯拉夫自己类型的社会主义的形成。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