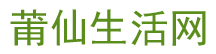在PA的校园日常作品的创作文脉中,【来自多彩世界的明天】(下称“多彩世界”)有着两点截然不同之处:第一,作品将主要舞台搬到了城市之中,而与其他以描述微型社区的作品拉开了距离;第二,作品引入“未来”这个话题,并非【凪止】一般以5年为跨度的同代人的物语,而是将时间拉长到60年、两代人的尺度。恰是这两个凸出的要点,成为切入作品文本的关键。
PA的作品一贯是有很强的乡土色彩的,【凪止】中的海村与渔村世界;【白沙】中的冲绳南城市;【花开物语】中的汤涌温泉……在讨论PA的一系列作品时,这样的乡土性要素是绕不开去的。且剧中的少女最终多少怀着对于乡土的感情而完成了自身的蜕变:
【花开物语】中少女最终凭借着对于温泉小镇的体认串连起了母女三代间的情感维系,最终与人和事和解;【白沙】中来自东京的少女最终与冲绳地域互相承认,找寻到自身的意义和归所;特别的,在【凪止】中,少年少女彼此的思念的情感使得冰封的海面重新潮涌,他们切实地改变了小镇的面貌,而凭借着自身的行为(或是自身的根本属性)与海村和渔村的微观世界产生具体切实的联系。
这一点上而言,作品对于乡土性的重视与不断阐发恐怕也与身处富山县的PA独特的空间坐标和对于自身身处之所的体认有着紧密的联系。
然而【多彩世界】多少是特别的,故事的舞台被搬到了城市,这与传统的乡土物语的叙事间产生了冲突;其次,在作品具体的行文叙事中,少年少女们在城市中的生活似乎并没有体现出他们对于这座城市的独特体察和依恋,以至于故事的大貌似乎可以被搬到任何一座城市中去:东京、大版、京都……
尤其是,城市本身是无机质的构成,并且城市是独特的、是异质性的空间,加之东亚战后城市建设的高度同质性(见伊恩布鲁玛【亚洲主题乐园】(【Asia World】),纽约书评官网),使得人们对于城市的体认只会是对于这一特定场域的体认,或是说对于城市生活方式的体认,而决难与任何具体的现代城市产生实质性的联系。这在本作的行文中,便体现为观众似乎难以在作品的行文中看到少年少女们与故事舞台、长崎的文本场域间的联系。这种PA作品中一贯叙事主题的缺席几乎被视作是一种遗憾。
果真如此么?不尽然。从多种视角而言,本作依旧是一部很典型的PA式的校园作品,本作的行文叙事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PA一贯的乡土性要素,而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前文所言城市意象的诸多负面因素。并且,作品中的少年少女也同样在相当程度上建立起了与作品舞台间的联系。而作品中如此“长崎(的乡土)性”(我们不妨这么称呼),恰在作品舞台的空间建构中体现。
想要回答“作品是否具有乡土性”,无非就是回答“为什么作品舞台非长崎不可?”以及“作品中的少年少女是怎么与长崎这一故事舞台建立起联系的?”
在解释作品的空间性是如何发挥效力前,我想先简要地阐发作品的舞台,长崎,自身的空间属性。长崎以长崎港和临港的小块平原为中心向两侧的坡地不断扩展,最终形成了以平原和浅坡地区为主要构成的市区和在山坡上层层垒叠的居民区以及学校,这使得从居民区的各处眺望便能够轻易地看到近处的长崎港和原初绿野缭绕的群山。同时,长崎市内地势起伏大,造成了从山坡往下看似乎离港口很近而内部纵深极大的情形。
认识到这两点后,回到文本中,我们便能够轻易地认识到这两种特质是如何影响以至于左右作品的行文的。在11话末,女主人翁和男主人翁互相通过亮灯彼此知悉,并最终冲出门,在观景台前相拥。分析这一幕的构成时,两个要素是比不或缺的:
首先,恰是因为长崎具有的市内地势起伏大且整体上居民区分布在山坡上的缘故,女主人翁才能够开窗清楚地看到男主人翁家的窗口,两人这才能够进行接下去的步骤;其次,两人实际距离离得非常远,这同时保证了只能靠开关灯来打信号,同时也让之后渲染情绪的日剧跑能够切实地发生,并最终使相拥的一幕落在了观景台前。
最后一只飞出的纸飞机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原本平飞的纸飞机因为男主人翁已经向女主人翁跑来而向下滑翔,恰是因为这样的提示才使女主人翁知晓向自己飞奔而来的男主人翁,从而成就了接下去的一幕。借以此,作品的舞台得以切实地参与进作品的行文中去,非长崎无以成就这一幕的发生,作品的“长崎(乡土)性”也有了初步的安放的空间。
但仅有这一幕是不够的,前文的论述只保证了非长崎不可,而没有证明作品中的长崎文本空间具有的乡土性。而后者,则同样在女主人翁向窗外探的一幕得到了满足。作品的两个特征是很需要关注的,一是女主人翁的心情常常通过拍摄长崎天空的空镜头体现:
在第10话女主人翁情绪低落的时候,在观景台上,镜头一转以朦胧的凄惨的玫红色的日暮为收尾;在确定学园祭的魔法活动后,走在回家路上的琥珀和瞳美被浓重的深绿色的山坡和深蓝的天空包裹;就连结局,女主人翁的自白中,“水是蓝色的真好,天空是湛蓝的真好”,同样离不开景色对于心情的衬托。
而重要的是,在作品的城市空间中,自然的景色占据了异常多的比重,而同样的,长崎的城市空间则似乎被折叠了起来。
记得上文中对于长崎的城市空间的描述么,狭小的城市区域被高低起伏的长崎城市空间所遮掩、折叠,而在作品主人翁们主要活动的由居民区和学校营构的山坡上向下眺望,则能够轻易地看到近处的长崎港和原初的群山绿野,就连身边也被山顶的绿植所环绕。在长崎这一特定的文本空间中,恰是由于其独特的空间性,文本中的城市被折叠,而相对应的,城市之外的大片湛蓝的天空、原初的港口与山坡、近处的绿野,晚上的星辰,这些要素被特意强调、放大。
这样的一退一进中,城市性的要素被淡化,自然性的要素被引入。在一个特定的语境下,制作组在女主人翁家和学校间营构出一个微型的不稳定的自然性场域。而恰是这些自然性的要素,给乡土性留下了叙事空间。
那么,具体联系起作品叙事的乡土性要素是什么?是烟花。首先,女主人翁是“无根”的。严格意义上来说,女主人翁并不具有“故乡”:她身在城市,对城市和自己生活的社区没有深刻体认;同时,她的创伤经验使得她并没有留下足够多可供怀旧的记忆与生活经验,这样一种内心漂泊的流动的经验被认为是一种现代性的具体体现,也就是人的无家可归。这导致女主人翁在未来世界中的彻底的失格(Lost)。
于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琥珀将之送回“当下”,便有了一种在人与人联系与微型社群尚未完全解体时通过使女主人翁再次经历(re-experience)这样的生活方式汲取足够的生活经验以完成一种自救,而非通常意义上的对于过去美好生活的怀旧促使琥珀将女主人翁送回过去。
这点暂且不表,接续上文的叙事语境,这意味着,只有少数经验成为了女主人翁的故乡经验的构成,而烟花无疑是制作组采纳的最重要意象:首先,烟火大会作为一种每年按时举办的活动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的代表;其次,女主人翁的烟火经验贯穿了她的生命历程,有和母亲一起观看烟火,有在母亲离开后自己独自背对烟火,有在穿越前的17岁独自参加烟火大会(这样的经验一定有很多次)。于是,烟火成为了具象的女主人翁的“乡愁”意象。
于是,琥珀在第四话中施放的烟火成为了融入微型社群的象征,第十二话学园祭后的烟火成为了一种集体生活中的共时性经验,成为了后文中被怀旧的对象,而在13话穿越回“未来”的花火大会,则有了生活经验的复生与对于不久前的集体生活的深刻怀旧的意味。烟花成为串连起女主人翁心路历程的重要意象,而恰是在象征着寂寥的漫天繁星和珍贵记忆的花火所共同具有的苍穹之下,女主人翁的乡土性有了其具体安放的坐标。
就此,我们可以说,【多彩世界】,仍是一部被安放了“回不去的故乡”的深刻愁绪的作品。不同于【白沙】中被拆毁的旧水族馆,或是【花开物语】中关闭的旅馆和温泉镇这一“回不去的故乡”,抑或是【凪止】中被怀旧的一切未发生时的情感,【多彩世界】中,被怀旧之物成为了数月间形成的生活方式与关于18年的微小世界的记忆所组成的全体、雪花球中的世界,成为时空维度上的“回不去的故乡”。
【多彩世界】在时间上的讨论成为作品又一个与PA校园日常作品传统间不同的要素。诚然,从最一般的视角而言,本作的时间穿越要素成为本作开篇一个非常好的话题,在校园日常的标签之外加入了更为新奇的内容。然而笔者则将目光放在了另一个聚焦点上:为什么是未来?为什么是60年?
日本文艺传统中,穿越题材在短短百年的日本文艺史中占据着一席之地。尤其是战后经济腾飞,60年代后的经济繁荣引发了对于大正意象的重新解读,大正被以社会民主经济繁荣的面貌大书特书,掀起了对于大正文艺题材的建构和一系列“穿越回大正”的作品涌现。较为新近的有YOASOBI的【大正浪漫】mv、结城弘老师的【摩登男女】等。这揭示出日本穿越题材的两大重要传统:一是以现代穿越回过去的叙事居多,二是穿越目的地一般为文化视野下值得自豪的历史时期,比方说明治开化的幕末时期,比方说文学视野下的大正民主时期,等等。
在这样的视野下,本作的叙事便显得有些奇怪:一方面采用了从未来穿越回现代的题材;另一方面穿越回的“当下”似乎并不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时期。尤其是以60年为时间跨度,穿越回祖辈的文艺传统中,不乏有从当下穿越到战后(繁荣)时期的作品出现。这就使得本作的穿越设定有了反语的意味。
穿越回过去与同龄的自己喜爱的祖辈一起生活,这样的题材创作恐怕是怎样也无法绕开创作者的自身经验的,所以与其说本作是一部以穿越为噱头的作品,不如说,本作的行文在一开始,就有一种深刻的怀旧色彩,而在最终的呈现上,则将创越的行文叙事与作品的校园日常相衔接得到的成果。于是,本作的叙事,算上60年两代人的跨越,就有了一种“从“未来”穿越回“现在””=“从“现在”穿越回60年代”的意蕴。
不如说,这才是潜隐在作品行文中的真实的叙事意图罢,穿越回过去,与自己的祖辈相见。如果真能按照真实的叙事意图来拍一部【虞美人盛开的山坡】的作品恐怕会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本作无论如何也没办法实现。从这一点往下阐发,这样的两次穿越,便有了一种联系当下与城市或是家族性历史的意蕴。尤其是作品中几乎没有发生变化的城市景观的整体构造,都在隐隐诉说着与当下进行对照的意图。
还有一点,作品的结局设置了女主人翁扫墓的一幕,这一幕笔者坚持这是在纪念男主人翁。就算不是,那么结局不让女主人翁与其他如今已是老爷爷老奶奶的夕日同窗相见,也足够体现制作组的趣味。
事实是,60年和两代人作为一种“隔”,已经从根本上彻底否定这样的“再见”的意图,就算能够相见,这也是足够不知趣味、煞风景的。所以,从行文上来说,是不可能再见的。分别的苦痛因为无法再次相见而得到了某种保证、某种恒固性。非此无以承担起作品情感堆叠的分量,13话开篇男主人翁苦痛的心情便也变得轻浮。这是不可以的。
同时,这一幕还具有的双重意蕴是,以现实中相见的否定凸显回忆与承载心情之物的重量。男主人翁跨越时空的思念,凭借着绘本的结局彩虹覆盖的企鹅而得以传递。这样的爱护的心情,通过女主人翁的救赎,具有了某种神圣性,单薄的保质期短的情爱和你侬我侬,通过这一幕变得崇高。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样的结局已经足够足够好。
时间、空间、心情,构成了【多彩世界】的全貌。
10月26日